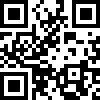你见过乳癌术后的女性身体吗?可曾想象她们如何穿内衣?
仅2020年,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42万,其中近九成患者接受了乳房切除术的治疗方案。而术后身体,一直是人们无从想象的部分。翻译《洛丽塔》、写小说的于晓丹,半路出家做内衣设计近二十年。今年3月末,她在同名公众号上发表文章《一款乳癌术后文胸的诞生记》,引发人们对乳腺癌术后女性身体需求的关注。
短短一个月内,这件特殊的内衣定稿、出厂、招募试衣志愿者,在北京完成了三场线下试穿。藏在衣衫之下的乳腺癌术后患者,一个个出现,集体走向她。5月27日,于晓丹为乳腺癌术后女性设计的内衣,随着她的黑色箱子从北京来到上海。虎丘路5号,环形落地窗外是近在咫尺的东方明珠,我们接待了27位乳腺癌术后试衣志愿者,现场静水深流。

1.
于晓丹本计划前一天下午抵达上海,这样可以有充足的时间熟悉场地、整理内衣。一场暴雨让航班延误了7小时,她整夜没有睡好,黑框眼镜下叠着黑眼圈,写作者气质扑面而来,慢声细语,认真。黑色拉杆箱打开,内衣一片片,还是工厂连夜赶制刚出货的模样。
试衣助手是她内衣课的两位学生,听她徐徐地讲:“这是患侧,这是健侧。样衣用来试穿,大货可以免费领走一件。”乳白色的内衣像棉花似的铺开来。
上个月北京三场试穿,都在于晓丹家中进行。“我家是完全敞开的,大家一起穿,互相看,互相聊天。”眼前的piu lab是相当漂亮的场地,开阔,采光好得充满呼吸感。但是那么透亮的落地窗,对乳腺癌术后患者意味着暴露,没有安全感。于晓丹将白色棉布围拢,试衣的区域暗下来,变得私密。
她猜测,上海这场参加者更年轻、身型偏小只,所以样衣尺码准备最充足的是M号。没想到,预判不够准确。

2.
10点半首场,第一名提前一刻钟就到了,一位五旬上海阿姨,着黑色蕾丝衫,蓬蓬的伞裙,短发,烫着卷。
很快,80后的思思也来了,正懊悔自己匆忙间把帽子落车上了,她指着脑袋笑说,“现在我的发型是一颗海胆。”也有70岁的奶奶,银发一丝不乱,抹着浅桃红的唇彩来,女儿不在家,她不会用手机,也不知道报名没成功,害羞地走进来问:这里是不是能试内衣?
“她们都不怕。”上午第一场结束后,于晓丹立马决定把试衣区域拉开,让更多阳光透进来,镜子闪闪立着。所有可用的椅子被集中放在等候的区域,现场像沙龙般热络起来。

33岁到70岁的女人,围坐着分享治疗经历:化疗的药水,难以抬举的手臂,体重的起伏...其中一位患者,自告奋勇当了整天的志愿者。她苦恼,头发在化疗结束后长成了卷毛。周围几位女士连声说,好酷啊,我想烫都烫不出这种卷。
最后,聊到了乳房。
27位患者,无一例外接受了单侧乳房切除或双侧全切。
乳房切除术,是目前乳腺癌治疗中最常见的手段。2014年柳叶刀发布的中国乳腺癌近况报告中显示,全国范围内乳房切除术占到原发性乳腺癌手术的88.8%,这意味着有九成乳癌患者接受了单侧乳房切除或双侧全切。
抗癌的故事被书写过多次,术后的身体沉默地散落到人群中。我们人的两眼所见视野在124度,水平视角最大可达188度,在日常可见范围之外,这些身体已经被忽视太久了。
3.
于晓丹和两位助理站在白色幕布里侧,27位试衣志愿者一个个按序入内,静静褪去衣物。身体展露在阳光之下,有些人丰满,有些人瘦削,有的人大笑着聊起身体的疤痕,有的人收拾好自己的内衣,不让他人触碰。
相似的是,缝缝补补的印记,像汛后的河道一样清晰,蜿蜒在她们身上。
piu lab主理人狗蛋回忆第一次看见大姨乳癌术后的身体,“我当时脸上努力表现得镇定,其实心里整个翻江倒海。”

2020年,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(IARC)最新数据显示,全球乳腺癌新发病例高达226万例,已超过肺癌。仅去年,中国有42万例乳腺癌新发病例。如早期诊断,及时选择手术治疗,患者五年生存率达到80%以上,预后良好者生存时间可以达到20-25年以上。
对旁人而言撩起衣摆后的一次剧烈震荡,意味着她们与身体凹陷共生的日子才开始,隐秘而漫长。
一开始,身体非常直接地受到影响。切除一侧乳房后,身体的失衡感就好比背一只永恒的单肩包。为了保持基本的平衡和美观度,她们尝试佩戴义乳。只是,义乳能够仿真一个看似正常的身体,却不能真的保护她们回到正常生活。
多位患者表示,义乳的材质又闷又厚,分量重,佩戴后患侧比健侧沉,又没有合适的内衣足够承托,肩膀连着背脊一整片,很快就吃不消了。没有合适的内衣穿怎么办?有位母亲索性用自己女儿的旧内衣,加棉片缝制成“独家款式”。
试衣过程中,记者听见她们轻轻述说生活的流失。穿天蓝色衬衫的阿姨忘不掉,当她像往年夏天一样去游泳,那天却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“站在泳池里,好像所有人都在朝我看”。立马有人附和,“是呀,想游泳,泡温泉,但一想到要去更衣室,那个画面。”话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有声音怯怯地附和:还有家居服。天热了,在家不想戴义乳,又怕吓到家里人。曾经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场景,都失去了安全感。
她们都爱美,喜欢穿漂亮的V领、一字领、小方领,因为伤口与凹陷,术后一律换成了宽松、领口到锁骨以上的圆领衫。思思以前买很多日系少女风内衣,带薄纱的那种。“现在都不能穿了,空空的。”她只好去买大码内衣,背心式,可以从脚套上来。有三十出头的时髦女孩做了乳房重建,她不再穿内衣了,因为没有乳头。
试穿最后一位是33岁的西西,又飒又酷。“我本来就没什么胸。”但她想念自由自在穿吊带衫的时光,术后曾花四五千元买了一款德国进口的义乳,却发现无法贴合自己的身体而作废。
最终她穿上S号的乳白内衣,包裹得刚好,配卡其阔腿裤意外时髦。我们都惊呼,好看!你可以直接穿背心出街了!她开心得手舞足蹈。
4.
于晓丹工作室设计的这款术后内衣,有黑白两色可选,前后开,肩带有8公分调节余地。其他,看似和普通内衣无异。“面料一摸就知道很好。”看到上海阿姨用手指摩挲,我们都忍不住去摸摸看。
与市面款式最不同的是模杯。试衣时,于晓丹会根据每位试衣志愿者的身体情况选择内衣的尺寸,收缩肩带,用薄厚不同的模杯分别调整患侧与健侧,帮助身体达到平衡,以得到更好的承托力。

于晓丹曾在《内衣课》书中写到,内衣是最好的心理医生,越是柔软、轻薄的东西,就是越有着超越一般的力量。这一次,一件内衣要去治愈的对象,前所未有真切、具体。
一对从江苏盐城来的母女,仔仔细细试了一个多钟头,女儿和试衣助理都觉得,完全看不出异样了。母亲前后四顾照镜子,还是觉得哪里空空的。
于晓丹后来再想起这位母亲,提到存在一种永远不能感同身受的视角。旁人从正面、侧面看,可她们是低头往下看,便能清晰地感知到身体凹陷的每一处边缘,日日夜夜,如影随形。
这件术后文胸仍有需要打磨的地方,无法一口气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。但至少,她们不再是被忽视的群体。
关于乳癌术后女性的身体到底需要怎样的考量,于晓丹有着文字工作者的温度与情绪,太多故事让她流泪,试衣时会慷慨留下手机号方便患者联系。
于此同时,作为内衣设计师,她也像纳博科夫写《洛丽塔》那般,研究与思考,在做着一件非常理性的活。

上海试衣总共举办三场,周末两场在上海活动组织者JUAN的家。老房子里日光四溢,我们聊起这次项目的细枝末节,于晓丹数次落泪。
Q&A
大多数人对“乳腺癌术后女性穿什么内衣”是无从想象的,六场试穿中你看到的她们,是怎么穿内衣的?
全是DIY,各种乱七八糟的DIY。她们很难买到一件完全合适的文胸,必须自己动一下手脚,有的人在里面塞纱布,有的人做了一个小小的、像饼干一样的东西垫在腋下,有的甚至在文胸背面加一个小兜兜,再把义乳放进去。她们能为自己做的事,就是首先解决外观上的不平衡。
从最初的设计理念落实到最后的成品也许是一个变动的过程,线下试穿后有什么新的发现与想法?
是的,每个人的身体都很不一样。这是个特别特殊的人群,平时你看不见她们在哪里。只通过图片,数字,不足以了解活生生的身体。我的好朋友确诊乳癌术后,我们说她是用生命在成就这件内衣,的确是这样。
最开始设计的时候,我们觉得很多人在切除手术后都是会去配义乳的,所以我们把义乳放在整个内衣的构建里面思考,更多考虑如何让患侧这一边有更大的承托,让义乳可以不那么往下坠。实际试穿之后我才发现,她们都急于想摆脱义乳。戴义乳会出汗难受,皮肤发红,有的人因为比较丰满,可能还造成心脏不舒服。
在北京第一场试穿,有个女孩突然之间说了这么一句话,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义乳?我们就不需要义乳了,再不需要了。我从来没想过,可以让她们丢掉义乳。
所以我们立刻重新调整了设计,感谢我们的供货商也非常配合,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,连夜加班开模,把现在这件样衣做出来。我们设计了一种实心杯,取名叫“自在杯”,给她们试穿时发现效果更好。

为什么目前市面上已有的义乳产品无法宽慰到术后女性?
其实义乳工厂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到了,从分量到尺寸,甚至手感,有很多形状款式可以选择。昨天我路过一家内衣店,大玻璃上就写着,他们在做一款非常逼真的义乳。
但是,她们需要逼真吗?好比假肢,假肢逼真有它的意义,接上后可以走路了,所以需要外形逼真。但乳房切掉以后,假乳做得再逼真,它也无法承担乳房原本承担的功能。抛开外观来讲,乳房有哺乳的功能,在两性关系中也有存在意义,这些都是义乳无法承担起来的。
短时间内密集接触女性30~70岁女性的术后身体,也是你不曾有过的经历,是否有对女性身体产生了新的视角?
说实在,时间特别紧张,这次我可能都没太仔细看她们的身体整体,我看到更多的是伤口,都在观察她们的伤口到底是什么样的。
我的好朋友M乳癌术后的伤口,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。北京场第一场试衣之前,我们团队有一个男生就跟我说,你必须要克服这个心理,你必须要看这个伤口,所以从第一个试衣患者走进来的时候,我才下定决心,我一定要看。但也挺出乎意料,真正第一次看的时候,没有觉得害怕。反而很专注在研究她们的伤口到底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有的人这么长?为什么有的人淋巴挖了那么多?淋巴最大程度能挖到什么程度?我脑子里在研究这些,像一个医生那样看她们的身体。
让你印象深刻的试衣志愿者?
昨天,我刚收到一份问卷,那个女孩30岁,填的年龄是30岁以下,手术已经做了10年了。我当时一看,天,这是什么状况?
其实要说印象深刻的,都是一些问题。比如说现在这一款是更适合C杯以下、相对来讲体型小一些的女性。但实际试穿后发现大码需求还挺大的,尤其上海。
上海的女性大尺码需求反倒比北京更多,上海有更多爱美的年长女性,体型也更丰满。我当时完全没想到,本来是觉得上海可能M码会居多,但实际上是L和XL更多一些。
如果原本的罩杯尺码越大,切除以后,健侧和患侧反差也越大,凹陷的感觉就会更加明显。我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,要怎么帮她们弥补?
她们的身体和遭遇都非常特殊,您作为一个写作者是否会尤其敏感?
唉,哭得太多了。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,我本身会很敏感,想很多,很细。出发上海前,我接到一个山东患友的电话,她女儿推荐她看了JUAN(上海场活动组织者)写的那篇文章(《为战胜过死亡的勇士,做一件最柔软的盔甲》)。她跟我说,她一边看一边大哭,我在电话这头听了一下子不行了,也跟着一起大哭。我老公就在旁边说,你不能老这么哭,人家正跟你通话,你就开始哭。
包括那天试穿志愿者招募的微博一发出来,好多大v帮转,下面的留言我几乎看一条就流一次眼泪。有的人说,我从来没想过我妈妈会不敢开灯洗澡,可她现在已经走了。这种事情真的没办法(不哭)。到后来我就说你们(试衣志愿者)最好是给我发微信,微博评论我也暂时不看了。
不管怎么样,我们现在有了这么一款产品,至少能开始帮助很多人了。以前做设计都是我们要去寻找用户,现在做这个项目之后,我发现是她们在找我。她们在不断追着你要快快快,夏天到了我们穿什么?有患者刚结束化疗,下个月要返回工作岗位了,追着我问,怎么办,穿什么啊?

其实看到你公众号上有写到,这件内衣的设计生产因为疫情年、资金的一些问题,还是经历蛮多困难的?
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快做不下去了,包括身边的团队,都觉得这不是一件能走太远的事情。到底要怎么走?怎么往下走?我的好友M是术后内衣的第一个试穿者,她穿上以后的那天,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。她老公看到第一眼只说了一句,又跟你生病之前一样了。
我一下子就意识到,这是一件值得做下去的事。
之后也会以这个特殊群体为受众继续设计内衣吗?
会的。大家现在会越来越发现,乳腺癌虽然发病率很高,切除比例也很高,但是乳腺癌也是一个存活率最高的癌症。很多人只要度过了前面的危险期,即便是复发,再做手术,都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生命周期,所以她们面临的是术后生活的全部问题。
能来到试穿现场的,已经克服生死这一关,并且希望着自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,还有她们追求美的愿望,我是觉得她们太勇敢,太了不起了,比我们要勇敢很多。所以我现在特别希望能够给这些人更多的陪伴,生活中各类场景的陪伴。
其实女性身体有很多隐患,很多都是无法对外说的,这些事情以后我们都要解决。原来我们都在做时装,所谓的fashion,做了这么多年,我想是时候从时装回归到服装本身了。服装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?最早它是解决人类遮羞的这么一个问题,是实用性非常强的存在。那我们是不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设计师,去关注到这些群体,做些有用的设计?
截至今日,北京、上海的免费试穿活动已圆满结束。这件特殊的内衣将在6月7日开始测试性发售,6月18日正式上线,目前已有不少全国各地的线上患友顺利下单。接下来,于晓丹团队正计划带着这件术后文胸去更多城市做体验活动(6月在武汉、太原),继续和患友见面,帮助她们穿戴内衣。有需要的读者可移步于晓丹同名公众号获取更多动态更新。